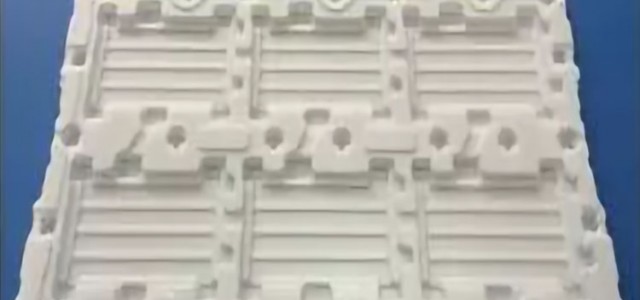李子柒引發(fā)的是文化共鳴
筆者在網(wǎng)上讀到一篇有趣的英文文章——“Li Ziqi Is on My Apocalypse Team”(《在我的末日生存小隊(duì)中,要有李子柒》),作者是位單親媽媽。她說(shuō),像許多從未經(jīng)歷過(guò)戰(zhàn)爭(zhēng)或席卷全國(guó)性大災(zāi)難的人一樣,她一度認(rèn)為,在“大難”來(lái)臨之時(shí),想要保命,就要迅速囤積罐裝食物和武器。后來(lái),她讀到一位經(jīng)歷過(guò)科索沃戰(zhàn)爭(zhēng)的塞爾維亞人的文章,文中說(shuō),大難來(lái)臨時(shí),那些囤積食物和武器的人死得最快,因?yàn)樗麄円欢〞?huì)成為暴徒攻擊的首要目標(biāo)。其實(shí),你只需要一點(diǎn)點(diǎn)能夠支撐你逃出戰(zhàn)場(chǎng)的食物,然后找個(gè)地方安頓下來(lái),找個(gè)窩,種些食物,便可保命。這篇文章驚醒了這位媽媽,讓她認(rèn)識(shí)到,李子柒這樣的人有多么重要——她可以從無(wú)到有變出一個(gè)“家”,種莊稼、做飯、建房子、做衣服……“什么,你不知道李子柒是誰(shuí)?這簡(jiǎn)直太瘋狂了,她實(shí)在是太有名了”,作者感嘆道。
李子柒的視頻走紅網(wǎng)絡(luò)是2017年的事了,而最近她再次掀起熱潮,則是因?yàn)殛P(guān)于“文化輸出”的討論。近年來(lái),“文化輸出”這個(gè)話題持續(xù)升溫,從中國(guó)經(jīng)典外譯,到諾貝爾文學(xué)獎(jiǎng)的突破,到中國(guó)科幻連獲雨果獎(jiǎng),再到中國(guó)網(wǎng)文大舉出海,一直是眾人關(guān)注的熱點(diǎn)。然而,以筆者之見(jiàn),“李子柒現(xiàn)象”與其說(shuō)是“文化輸出”,不如說(shuō)是“文化共鳴”——那些美麗、溫暖的影像,仿佛一只輕柔的手,緩緩撥弄起一把已經(jīng)被現(xiàn)代都市里生活的人們放置了許久的木琴。
曾經(jīng)有一部風(fēng)靡美國(guó)的書(shū),名叫《草原小屋》(其實(shí)是一個(gè)共九本書(shū)的系列),是關(guān)于19世紀(jì)70年代一個(gè)家庭如何在蠻荒環(huán)境里生活的故事,既有艱辛,又充滿了智慧、歡樂(lè)和希望。一匹瘦馬,一輛破車,拉著一家人和一條狗,在美國(guó)中西部草原上游蕩。他們不怕荒野——有時(shí),將他們與狼群隔開(kāi)的只是一床棉被;有時(shí),媽媽會(huì)把風(fēng)雪中的大灰熊誤當(dāng)作自家的奶牛。他們四處安家——草原上,一堆木頭可以變成一個(gè)家;河堤上,挖出個(gè)大洞,也可以當(dāng)作家;他們自給自足——要吃糖,割開(kāi)楓樹(shù)皮,讓樹(shù)的甜汁流出來(lái),稍加熬制即可;要吃飯,就自己種莊稼。在曾經(jīng)的那個(gè)時(shí)代,在任何地方從無(wú)到有把“家”建起來(lái),幾乎是每個(gè)人的必備技能。
今天,在一些美國(guó)人家里,最重要的地方可能不是廚房或臥室,而是車庫(kù)。那里不只用來(lái)存放車輛,還堆滿了零零碎碎的工具。大人和孩子們,在那里敲敲打打,是一天中最開(kāi)心的時(shí)光了——小到桌椅板凳,大到電視、電腦,可能都從那個(gè)車庫(kù)里誕生。不過(guò)在現(xiàn)代社會(huì),或許更多的人,特別是我們這些被塞進(jìn)高樓大廈中的人們,家里并沒(méi)有那么一個(gè)“車庫(kù)”,更不知道它是用來(lái)干什么的。我們漸漸習(xí)慣許多人和許多的便利被堆疊在一起。現(xiàn)代都市給我們的生活提供的種種便利,一旦因?yàn)槭裁丛虮粍儕Z,我們應(yīng)當(dāng)如何生存下去就變成個(gè)大問(wèn)題了。
日本電影《生存家族》就寫了這樣的故事。生活在高樓中的一家人,每天被“囚禁”在自己能夠觸到的那一片小天地——超市、學(xué)校、公司,循環(huán)往復(fù),對(duì)于更廣闊的世界,沒(méi)有時(shí)間,也沒(méi)有心情欣賞。外公定期從遙遠(yuǎn)的鹿兒島寄來(lái)的新鮮蔬菜和魚(yú),對(duì)于習(xí)慣了超市售賣的速凍食品的一家人來(lái)說(shuō),簡(jiǎn)直是種負(fù)擔(dān)。忽然有一天,大家認(rèn)為理所當(dāng)然的最重要的兩樣?xùn)|西——自來(lái)水和電沒(méi)有了。于是,人們發(fā)現(xiàn),其實(shí)不需要什么核戰(zhàn)爭(zhēng)、外星人入侵,只是這兩樣基本便利消失,就可以釀成令現(xiàn)代生活癱瘓的大災(zāi)難。在這種情況下,這一家人,只好“從頭學(xué)起”,學(xué)習(xí)如何“生存”,學(xué)習(xí)一種全然不同的生活方式。還好,在一番痛苦掙扎之后,他們不僅撿起了“生存的本事”,更體會(huì)到,沒(méi)有了高樓大廈、店鋪商超,沒(méi)有了一眼望不到頭的貨架上花花綠綠、林林總總的貨物,生活反倒因?yàn)楹?jiǎn)單而變得安然、實(shí)在。
有兩位哲學(xué)教授合寫了一本小書(shū)《所有閃耀的東西》(All Things Shining),書(shū)中提到,“當(dāng)代人面臨的最深刻也最艱難的問(wèn)題,不是我們明知正確行動(dòng)的軌跡,卻無(wú)法遵循那個(gè)軌跡,而是我們似乎經(jīng)常根本就不知道一個(gè)好生活的標(biāo)準(zhǔn)究竟是什么。”
離開(kāi)田園久了的人,一定對(duì)那份“理所當(dāng)然”有著深切的向往。在那里,事事都有著它們應(yīng)有的“規(guī)矩”: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,春生夏長(zhǎng),秋收冬藏,一切依照時(shí)令而行。都市生活帶來(lái)便利,同時(shí)也帶來(lái)了焦慮和無(wú)所適從。林立的廣告牌、密密麻麻的店鋪,種種選擇,最終卻造成幾乎沒(méi)有選擇,因?yàn)槊恳环N選擇,好像總不是那個(gè)對(duì)的。李子柒的影像,卻令人們——哪怕是片刻地放棄或擺脫那些選擇。在那里,沒(méi)得選擇,要做,只有一條路:要吃面包,就自己先去做一個(gè)面包窯;要蓋蠶絲被,就自己先去養(yǎng)蠶;要睡沙發(fā)床,就自己先去砍竹子。想必人們?cè)谟^看那些視頻的時(shí)候,會(huì)得到一種初讀《魯濱遜漂流記》時(shí)一樣的快感——一個(gè)人從無(wú)到有,自給自足。魯濱遜的故事之所以能夠風(fēng)靡世界幾百年,想必主要?dú)w功于它所傳遞的那份“自立”的精神:不依賴于他人,不局限于小環(huán)境,憑借勤奮和智慧,做自己要做的事。大到在蠻荒之地建立新的文明,小到為了給年夜飯?zhí)硪坏啦硕H自動(dòng)手制作一份味道十足的臘腸。
毫無(wú)疑問(wèn),田園生活對(duì)于疲倦了都市的人們來(lái)說(shuō),代表的是“簡(jiǎn)單”,是安心之處。加拿大歌手、詩(shī)人萊昂納多·科恩(Leonard Cohen)在晚年時(shí),離開(kāi)燈光耀眼的舞臺(tái),躲到山上寺廟里去生活,每日砍柴、灑掃、吃飯。過(guò)簡(jiǎn)單的生活,便是修行。美國(guó)作家理查德·鮑爾斯(Richard Powers),原本生活在喧鬧的都市,還在世界名校任教。一天散步時(shí),他忽然遇到一棵參天大樹(shù),按照他的說(shuō)法,那簡(jiǎn)直就是一個(gè)“晴天霹靂”——一棵“有一個(gè)足球場(chǎng)那么長(zhǎng),有一所房子那么寬,和凱撒或是基督那么古老的樹(shù)”,在經(jīng)歷了多少人世滄桑之后,依然挺立在那里。在那個(gè)時(shí)刻,他仿佛得到天啟,于是決定離開(kāi)喧囂,辭去教職,去樹(shù)的世界里生活,還寫了一本以樹(shù)為主角的厚厚的書(shū)——《上層林冠》(The Overstory)。
田園,不僅是一個(gè)地方,一種生活,更是一種情緒。
有人質(zhì)疑李子柒的視頻中所展示的“田園”并非真正的“田園”。不可否認(rèn),李子柒視頻中的田園,與“汗滴禾下土”的田園相去甚遠(yuǎn),她的田園,更像是馬洛的詩(shī)《熱情的牧羊人致他的愛(ài)人》里歌唱的那個(gè)田園:
來(lái)吧,和我在一起,做我的愛(ài)人,
在山谷、果園、丘陵、田野,
森林,或是陡峭的高山
我們一起體味所有的歡愉
我們坐在石頭上,聽(tīng)
淺水邊潺潺水聲伴著
鳥(niǎo)兒曼妙的歌聲,看
牧人照看羊群吃草
我要為你用玫瑰做床
再配上千種芳香的花兒
我要為你編一頂花帽,
再做一件遍繡神木葉紋的長(zhǎng)袍
再?gòu)奈覀冏约何桂B(yǎng)的可愛(ài)小羊身上
扯下最好的羊毛,為你做一件長(zhǎng)裙
天冷了,再做一件襯里厚實(shí)的鞋子
鞋扣要用真正的純金
稻草和嫩藤編一條腰帶
裝飾著珊瑚和琥珀
如果這些歡愉能打動(dòng)你,
請(qǐng)來(lái)和我在一起,做我的愛(ài)人。
又或者是葉芝吟唱的那個(gè)《湖心島茵尼斯弗利》:
我就要起身走了,到茵尼斯弗利島,
造座小茅屋在那里,枝條編墻糊上泥;
我要養(yǎng)上一箱蜜蜂,種上九行豆角,
獨(dú)住在蜂聲嗡嗡的林間草地。
那兒安寧會(huì)降臨我,安寧慢慢兒滴下來(lái),
從晨的面紗滴落到蛐蛐歌唱的地方;
那兒半夜閃著一片微光,中午染著紫紅光彩,
而黃昏織滿了紅雀的翅膀。
我就要起身走了,因?yàn)閺脑绲酵韽囊沟匠?/p>
我聽(tīng)得湖水在不斷地輕輕拍岸;
不論我站在馬路上還是在灰色人行道,
總聽(tīng)得它在我心靈深處呼喚。
可以說(shuō),無(wú)論田園詩(shī)里的田園,還是歌手、詩(shī)人、小說(shuō)家眼中的田園,都不是真正的田園。因?yàn)檎嬲奶飯@與都市一樣,也處處是危險(xiǎn)、爭(zhēng)斗、痛苦。美國(guó)詩(shī)人羅伯特·弗羅斯特倒是個(gè)描寫“真正田園”的人,他筆下的農(nóng)村,當(dāng)然有美好,但更多的是艱辛,這里有小小年紀(jì)的孩子被電鋸?fù)淌呻p手,有相鄰而居的農(nóng)人彼此因?yàn)閲鷫Φ囊环忠缓炼鵂?zhēng)執(zhí)不休……
威爾蒂(Eudora Welty)的短篇小說(shuō)《旅行推銷員之死》寫到一個(gè)名叫鮑曼(Bowman,意思是“彎腰男人”)的推銷員,每日辛勞,四處推銷,一次在深山里偶遇一個(gè)特別的家庭,一對(duì)強(qiáng)健的夫婦,過(guò)著簡(jiǎn)陋卻充滿生命力的日子,與他們相比,他的生活簡(jiǎn)直毫無(wú)意義,更令他嫉妒的是,那女人還懷了孩子。“他吃驚地意識(shí)到這個(gè)房子里到底有什么——婚姻,有了果實(shí)的婚姻。那件簡(jiǎn)單的事。人人都該有的事。”但他沒(méi)有。他還要離開(kāi)這里,回到他的世界。半夜里,他起身,小跑著離開(kāi)這個(gè)充滿誘惑的地方。忽然,一陣心痛襲來(lái),他死在了黑夜里。
真正地遠(yuǎn)離塵囂,它的直接、強(qiáng)力,甚至殘酷、兇猛,恐怕是都市里生活慣了的人們所無(wú)法面對(duì)的。
電影《走入荒野》(Into the Wild)的原型克里斯(Chris McCandless)是一個(gè)憤世嫉俗的年輕人,他只身徒步在阿拉斯加荒野,試圖過(guò)上不受羈絆的生活。紀(jì)錄片《灰熊人》的主角提摩西(Timothy Treadwell),每年都花上大半時(shí)間去與世隔絕的自然保護(hù)區(qū),與灰熊生活在一起。最終他們都被蠻荒吞噬。
不過(guò),與上文中的田園或荒野相比,李子柒的世界其實(shí)要“文明”得多,也“安全”得多了。就像前文那位“末日生存”媽媽所說(shuō),因?yàn)檎苿?dòng)的基礎(chǔ)設(shè)施建設(shè)和開(kāi)發(fā),自來(lái)水、鐵路網(wǎng)絡(luò)、電、5G網(wǎng)絡(luò)等等,使得李子柒那樣的人能夠悠閑地生活。
陶淵明或梭羅式的安貧樂(lè)道是常人學(xué)不來(lái)的,而李子柒式的自食其力、苦中作樂(lè),倒是普通人可以效仿的。更為重要的是,或許李子柒的故事,讓許多放棄田園、盲目涌向大城市的人們能夠想起田園的美好,想起,其實(shí)幸福的生活并不在遠(yuǎn)方,而是就在我們身邊。
(作者:王偉濱,系河北科技大學(xué)副教授)